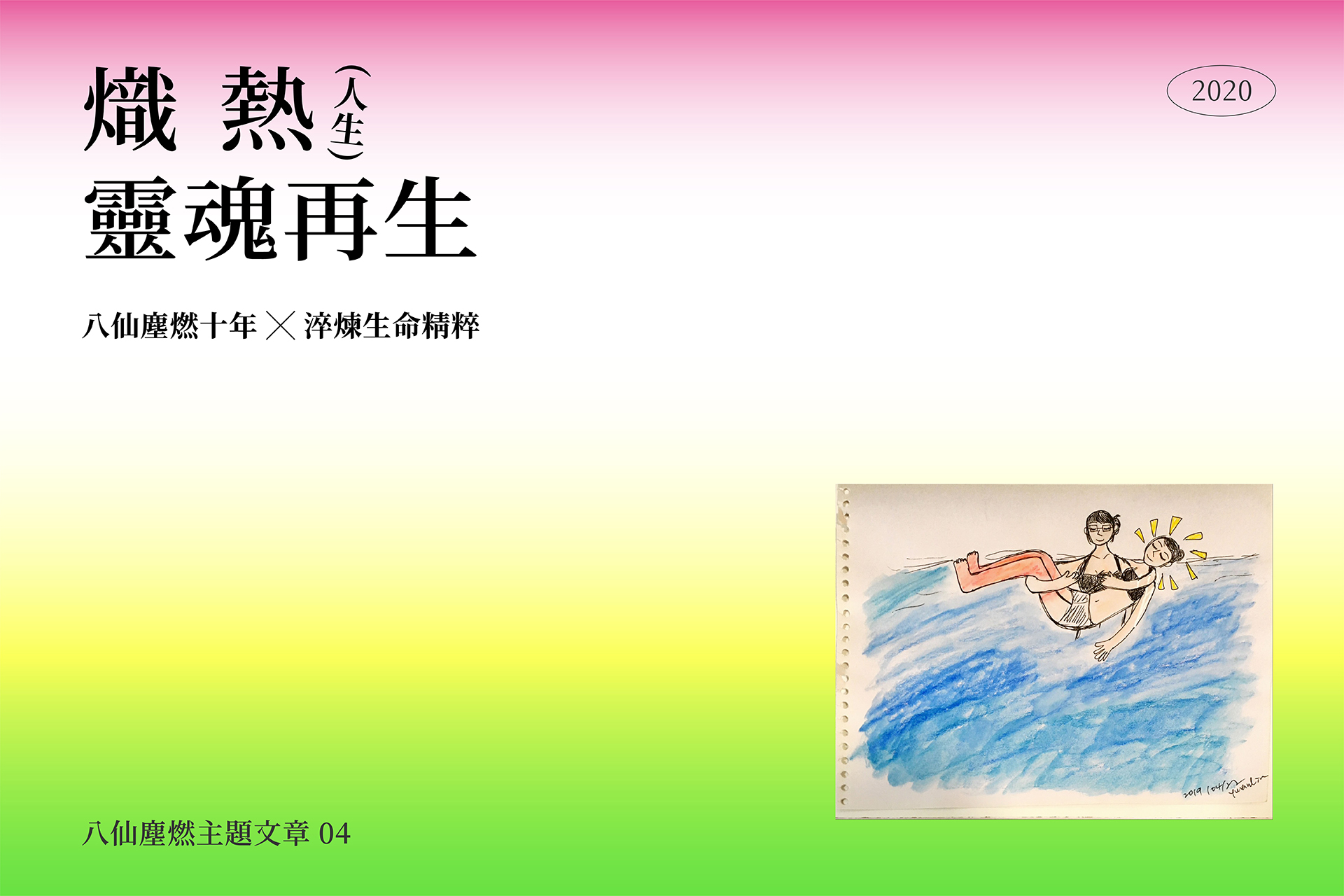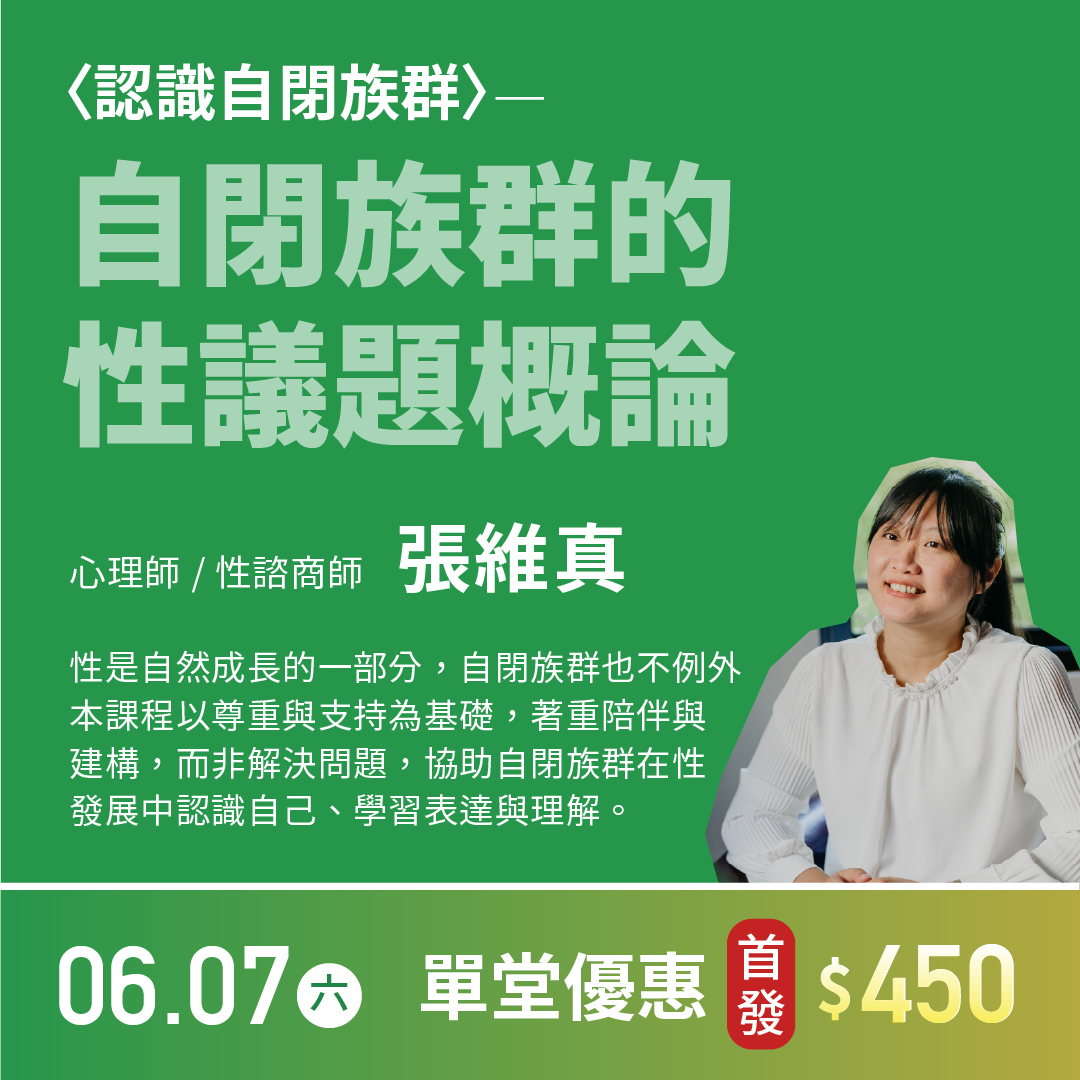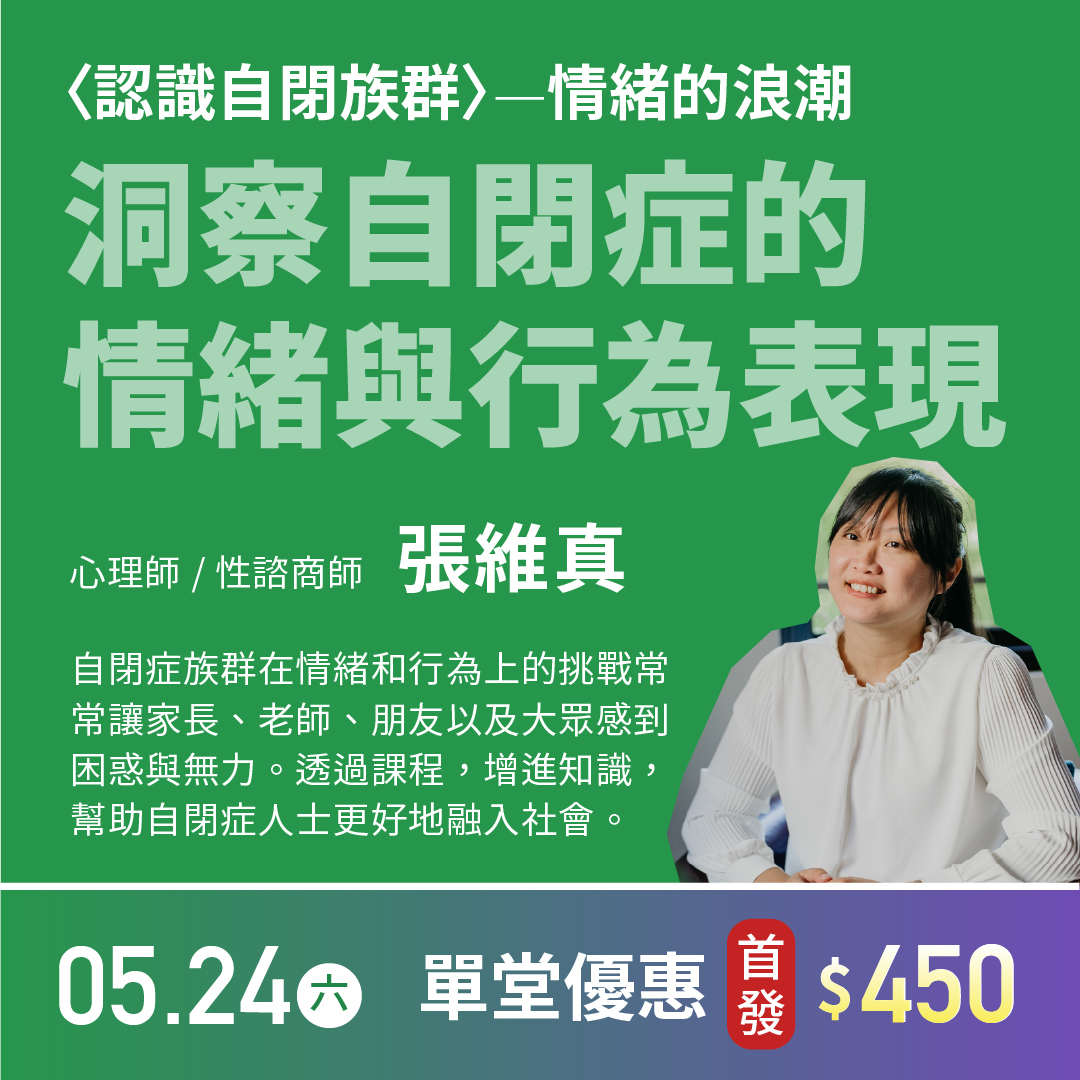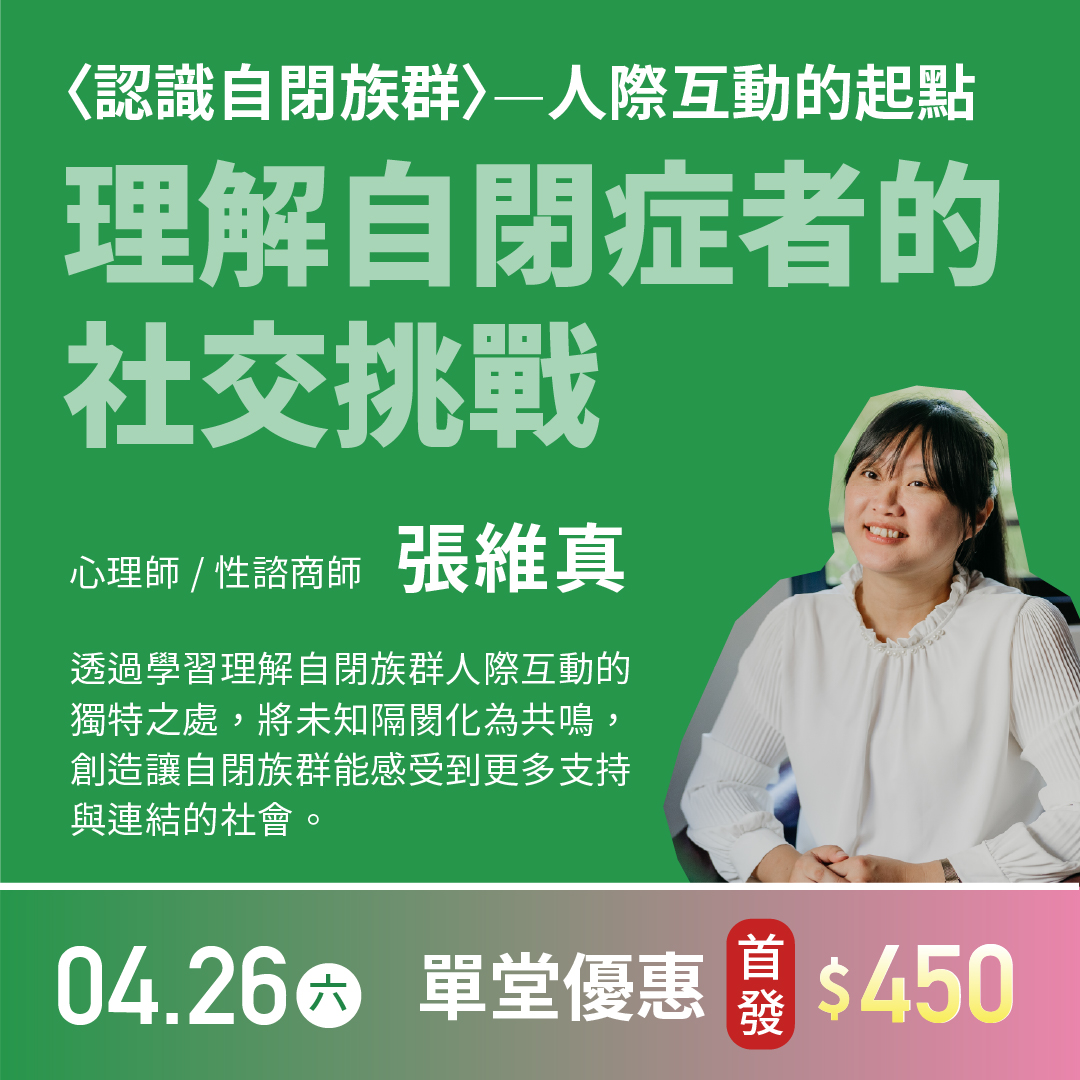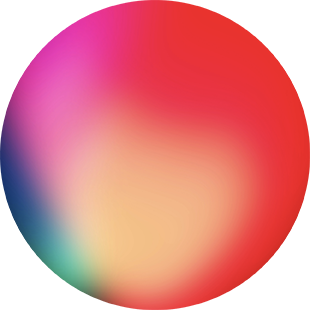孤獨」大概是從小到大,與我最緊密連結的情緒了。
小時候,看到同學追星,幾個女孩聚在一起吱吱喳喳,她們看起來無憂無慮,但我腦中想的卻是家裡的狀態。我可以在旁邊聽,卻總是不知道該怎麼融入,總覺得自己與這個世界有道無形的隔閡。
後來,經歷了性創傷與燒燙傷創傷,那種孤獨感變得更加鮮明。
創傷泡泡(Trauma bubble)與孤獨
燒燙傷意外發生時,我和一群人共同經歷了這場公共安全事故,但大多數人是和朋友一起受傷、一起復健,而我同行的研究所同學卻沒有受傷。我經歷逃生、經歷復健,明明身邊有很多人,卻總感覺這條路只能自己走。
當我與傷友聚在一起,他們年紀相仿、背景相似,多數人選擇休學專心復健,而我年紀比他們大,原本就不認識,出院後又回到學校繼續讀書。我們的生命軌跡看似相似,卻無法真正產生交集。
回到校園,和大家一起坐在教室裡聽課,腳上的疤痕傳來刺癢、抽痛,讓我分心。下課時,大家輕鬆站起來往外走,我的膝蓋卻還伸不直。即便我和大家做著相同的事情,內在仍清楚感知到自己的不同。
傷後不久,外婆意外過世了。在家族裡,我們很長一段時間無法談論這件事。即便媽媽與大姐輪流照顧我,我們維持緊密的關係,但我仍然感覺,他們有他們的哀傷, 而我,也有我的哀傷。
我們一樣,卻又不一樣。
我逐漸理解,這種孤獨感來自於「我清楚自己與別人不同」,而且我沒辦法假裝自己和大家一樣。

如影隨形的孤獨感
燒燙傷後的第三年,生活看似回歸常軌,我努力證明自己可以和大家一樣,創傷沒有改變我的人生軌道。我開始迴避談論過去,不願讓「現在的好」被「過去的不好」侵蝕。我告訴自己,這樣就好了。
然而,即便生活恢復正常,我仍然感受到孤獨感如影隨形。在伴侶關係中,有時覺得自己被愛,但又懷疑自己是否真的重要;即便在親密與性的互動中,仍然感覺有道無形的隔閡。
直到某一天,我問自己—— 我真的想過這樣的生活嗎?
走向真實的自我
我渴望真實。我渴望有人能看見完整的我,包括我的傷、我的脆弱,也包括我真心想分享的快樂。
於是,我開始運用資源學習。透過性諮商的學習、督導、與朋友與伴侶的對話,我開始允許自己直視過去的脆弱,並理解這不是對現在的威脅,而是「現在的我已經有能力涵容這一切」。
我開始練習肯認自己的好, 練習接收別人的肯定與讚美, 練習相信自己是值得被愛的, 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愛。
我逐步練習向他人敞開,接受來自伴侶、家人和朋友的愛與支持。我也逐漸修復對於親密關係的信任;
理解愛是一種連結,而我並不真的孤單。

走重建的路,持續前行
燒燙傷的重建之路,不只是身體的恢復,也是心理的復原與成長。 性健康不僅是身體的重建,更是情感的連結與心理的重塑。
創傷與孤獨不會消失,但它們不再定義我。
一步步,我學會更自在地做自己,也學會在親密與性中更自在。
如果你也正走在重建的路上, 請記得,你並不孤單。
每一段重建的過程,都是朝向更真實、更完整的自己邁進的步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