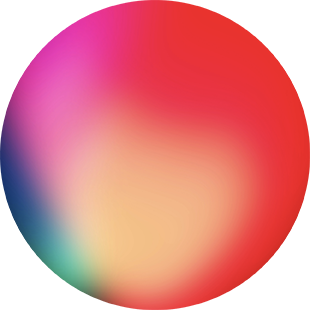2015年6月27日,那是我第一次走進八仙樂園,卻也是我熟悉的人生被徹底崩解的一天。
那天傍晚,我和幾位朋友進入了彩色派對現場,笑聲、人潮、音樂與五彩的粉末混雜在一起,空氣裡浮著一種青春與興奮。就在我牽著朋友的手跳舞的時候,火,忽然燒了起來。一開始我還以為是特效。兩秒後,我意識到不是。
我倒下、又爬起、再倒下。腳下的夾腳拖已經不知道哪裡去了,我赤腳奔跑,皮膚在火焰中剝離,痛覺與求生意志交錯著湧上來。我一邊喊「拜託,有水嗎?」一邊奔向泳池。有人不相信火真的燒起來了,有人笑著,有人愣住。
我跳進泳池,涼水帶來短暫的緩解,也同時把痛感刺進更深層的皮肉。我求著多泡一下水,但旁人勸我趕快上岸。有人用泳圈撐著我,有人撒水降溫,有人借我手機打電話,我用簡短的幾句話報平安:「媽,我在八仙,燒傷了,但我還活著。」
等救護車的過程像無限延長的地獄。陌生人組織起來,有人幫忙蓋紗布、撒水、有人用麥克風指揮、有人握著我的手讓我保持清醒。我被幾位陌生人抬著泳圈,移動到外面廣場,周遭是滿地的傷患與交錯的哀號。我記得有個媽媽含著眼淚看著我,唸著佛號。那一刻我知道我只能靠自己撐下去。不能昏迷、不能睡著、不能讓身體失溫。我的腳掌裂開、手指破皮、全身四肢和背部都是大面積燒燙傷,但我還是努力呼吸、努力清醒。
那是我第一次看見「資源」這件事不是抽象的詞,而是:有人幫你灑水、有人扶你一把、有人讓你報平安、有人什麼都不說只是靜靜看著你。是這些人,讓我活下來,也讓我在混亂中沒有崩潰。

送醫後我被插管,接上監測生命徵象的機器,送入加護病房。住院期間,醫護人員幫我清創、餵食、換藥、植皮。我在意識清醒與昏迷之間浮沉。當時的我,什麼都無法做,什麼也無法決定,只能「撐著」。
現在的我,回頭看那個當時的我,心疼得發抖,但也無比佩服她。她不是沒有害怕,而是在害怕裡選擇盡可能活著。那個「撐」不是逃避,而是她當時唯一能用的能力。她還沒學會怎麼鬆開、怎麼表達需求、怎麼哭出來,但她已經用盡她所有的資源:意志力、呼吸、信任他人。
能力建構取向,是我幾年後才遇見的語言。但我後來才知道,當時的我早就在做「能力建構」了。那不是口號,是活著的人每天在選擇的方式。
選擇不昏迷、選擇報平安、選擇相信自己會得救、選擇把希望交給陌生人——這些,都是能力。

十年過去,我學會了更多不同的能力,不再只靠撐。而當我願意回望當下的那一天,願意承認我多麼害怕、多麼孤單、也多麼努力,那個時刻就不再只是災難的開始,而是我「成為自己的起點」。
我想告訴每一個經歷過創傷的人: 我們不需要馬上好起來,不需要一開始就變堅強。 但請你知道,你已經在建構。 你已經在開始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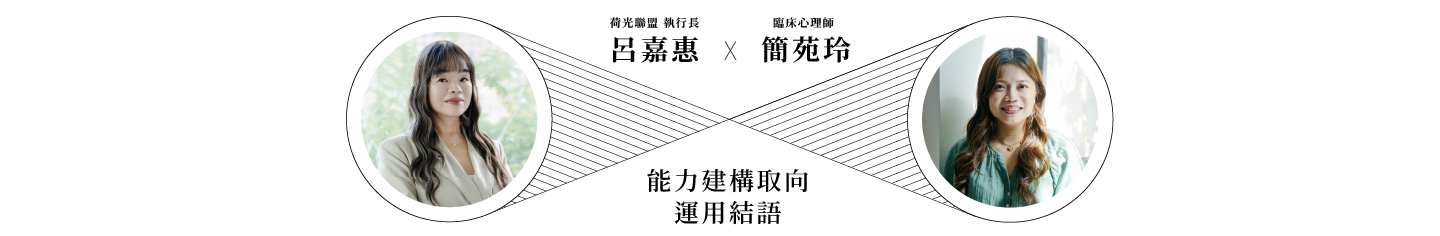
火焰中,妳本能啟動了⼈格脊椎最初的覺醒——分化;分化出自己的存在。
不是⽕焰塑造了妳,而是妳選擇在⽕焰中,仍然是自己。這是依附能力的最純粹開展:即使世界崩解,仍在內在握住自己的⼀條脈絡。
每一次痛覺呼嘯⽽來時,妳練習了情緒轉化力的源初節奏:把恐懼轉為呼吸,把無力轉為凝視。
在人海與陌生人之間,妳沒有消失,而是創造了人際共創力:用報平安、用手的觸碰,留住自己與世界的連結。
妳主導了資源生成力:不是等待救贖,而是一點水、⼀個眼神、⼀個泳圈,都成為活下去的延伸。
最重要的,是妳在無常中種下了人生洞察力的種子:生命不再是等待救援的故事,而是自己從碎片中,一次次重塑光的選擇。
能力建構,從來不是『要堅強』,而是——即使破碎,仍然存在。即使害怕,仍然選擇前行。妳,從那⼀刻起,已經不只是倖存者,妳是自己的創造者。